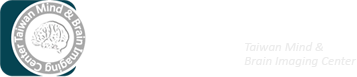本计画主要是想了解人们是怎么处理中文的分类词(C, classifier),例如「三本书」,与量词(M, measure word),例如「五箱书」,以及处理这些词语时大脑哪些脑区会较为活化。
许多语言学家,尤其是形式句法学家,认为C/M 应统合为同一范畴;然而也有许多学者坚称兩者应分属不同的類别。何万顺教授(Her, 2012)提出一个创新的数学观点来解释:分类词与量词(C/M)的关系是归因于他们在数学功能上的分与合,他认为C/M的共通点在于他们都扮演「被乘数」的角色,分类词以「三本书」为例,「三」和「本」之间是乘法的关系,也就是3 × 1,共3本书,值得注意的是,分类词代表的都是1,例如:本、只、颗等;量词虽然也同样扮演被乘数的角色,但是不等于1,例如「两打笔」,相当与2 × 12,共24枝笔。
这个理论不只对于语言学家来说很重要,也是心理学家们很感兴趣的议题,原因在于这个理论的前提是语言和数学之间密切相关,虽然语言和数学看起来像两种截然不同的认知能力,但是这两者都是透过符号来表征概念,例如:中文大写数字「壹」和阿拉伯数字「1」都是代表「一」这个概念,但是所用的符号却不同。过去的心理学家们也一直不断地在探讨数量概念究竟是以抽象的方式在大脑中表征,还是不同的符号分别有各种不同的脑神经基础。
对于C/M是否与数字处理有类似的神经基础,从既有的实验研究中并无法得到定論。在一个最新的fMRI实验中,Cui等人于2013年发现分類词的处理与工具名词(如:镰刀)较为相似,和点阵与数字相比,他们会引发左脑的额中回(left middle frontal gyrus, MFG)与额下回(left inferior frontal gyrus, IFG)较高的活化;而点阵和数字则是会诱发楔前叶(precuneus)与右脑的颞上回(superior parietal lobule, SPL)、顶叶顶下叶(inferior parietal lobule, IPL)较多的神经活动。这样的结果并非何万顺教授的数学理论所预测的,根据这个理论,会预期处理分类词与处理点阵、数字应有较相似的神经活动,例如,会诱发大脑右侧顶内沟(right intraparietal sulcus, IPS)有较高的活化,这是典型在表征数量时会有较高活动的脑区(Dehaene et al., 2003; Nieder & Dehaene, 2009)。
这有可能是因为Cui等人(2013)研究中所谓的分类词,其实包含了大量的量词,不仅未区分C与M,也未区分不同数值的M,例如:固定数值的「双」(2) vs.不定数值的「列」(n);此外,他们也没有排除掉在实验中受试者的判断可能受到分类词的语义属性影响。在他们的实验中,受试者会在萤幕上看到三组不同的词,例如:「一册」、「一张」、「一本」等,受试者须从萤幕下方的两组中选出和目标词语义较近的词。然而,由于分类词带有强调后方名词特性的作用,例如「册」和「本」皆是用于强调书本,而「张」则是强调面状,在他们的实验中,并没有控制不同分类词的语义属性,成为一个混淆因素,这也可能导致他们的研究结果发现分类词和工具名词的神经基础较类似,而非和数字较为相似。
因此,本计画先执行一个行为实验来厘清上述可能的混淆变项,首先,我们在实验中将代表不同数值类型的M区分开来,另外,我们将实验的刺激材料改良为最小对立体(minimal pairs)让受试者们选择,透过在每组词后加上相同的名词来限制C/M的语义属性,举例来说,受试者须从「一对耳环」与「一只耳环」中选择何者与「一副」语义较为接近,在这种情况下,「对」和「只」的语义属性就被「耳环」限制了,仅剩下数值的差异。实验结果发现,受试者们处理固定数值的C/M时,相较于不定数值的C/M,正确率较高,且反应时间也较快。这说明了,受试者们确实会以数值的方式处理C/M,尤其是代表固定数值的C/M(如:双、对、打等),至于不定数值的C/M(如:排、列,组等),有可能是这些词可代表的数值范围变异性太大,在这个实验的作业中,受试者们难以精确地进行比较。不论如何,在修正了Cui等人(2013)的实验设计后,我们验证了C/M确实代表不同的数值,更精确地说,C = 1,M ≠ 1,初步支持Her(2012)的理论。
接着,在行为实验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检验受试者们在处理C/M时的大脑活化情形。我们沿用Cui等人(2013)的实验设计,但是改良了刺激材料,透过使用最小对立体来限制C/M的语义属性,另外,由于受试者们如何处理不定数值的C/M尚待厘清,在这个实验中,我们仅采用固定数值的C/M作为材料。
结果发现,处理分类词和处理工具名词相比(图1a),会诱发较多活化的脑区有:包含右侧顶内沟(right IPS)在内的两侧顶叶顶下叶(bilateral IPL)、右侧额上回(right SFG)、两侧额中回(bilateral MFG)、右侧额内回(right medial frontal gyrus, mFG)、右侧颞中回(right MTG)、与左侧枕叶舌回(left lingual gyrus)。和Cui等人(2013)的研究结果不同,我们发现如Her(2012)提出的理论所预测的,受试者处理C/M比起处理工具名词,在右侧顶内沟(right IPS)会有较高的活化,说明C/M涉及数量处理历程。此外,我们的结果也发现,受试者在处理C/M、阿拉伯数字、中文数字、点阵时会共同活化的脑区如下(图1b):包含梭状回(fusiform gyrus, FFG)在内的两侧枕叶皮质(bilateral inferior occipital cortex, IOC)、两侧颞上回(bilateral SPL)、两侧顶叶顶下叶(bilateral IPL)、两侧额下回(bilateral IFG)、右侧额中回(right MFG)、两侧额上回(bilateral SFG)、与两侧脑岛(bilateral insulae)。与过去文献一致,大脑中的顶内沟(IPS)是以抽象的方式表征数量(Dehaene et al., 2003; Nieder & Dehaene, 2009),此外,最近的一篇整合分析研究也报告....详见全文